《烟火漫卷》是迟子建最新的长篇小说,它聚焦在哈尔滨,这座作家离开故乡大兴安岭后生活了30年的城市。
记者| 孙若茜
初到哈尔滨时,迟子建的写作与这座城市少有关联。她形容自己“虽是它的居民,但更像是过客”,始终都在倾情书写心心念念的故乡。直到上世纪末的《伪满洲国》,作为小说历史舞台的主场景之一,她才开始在作品中尝试构建哈尔滨,但它依然没有以强悍的主体风貌在她的作品中独立呈现。
十几二十年过后,在哈尔滨生活得足够久了,迟子建的笔才逐渐伸向这座城,于是有了《黄鸡白酒》《起舞》《白雪乌鸦》《晚安玫瑰》等作品。她说,要对一座城市进行完整的文学表达,只有到了一个恰当的时机,作家发现自己的素材积淀得足够驾驭这个题材起飞的时候,才能比较丰沛地表达对这座城市的感情。对她来说,《烟火漫卷》就是这样的表达,这是她认为的到目前为止和哈尔滨融合度最高的作品。
哈尔滨是一座自开埠起就体现了鲜明包容性的城市,迟子建写的正是生活在其中的人,他们之间的碰撞与融合。无论城里人还是城外人,犹太后裔、战争遗孤、退休狱警、小镇弃尸者、孤独的老人、伤痛的少年等,他们在哈尔滨共同迎来早晨、送别夜晚。他们在寻找,又被寻找——她说,这本书就是一场大大的寻找。有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谁,这是生命最大的悲剧。
作家构建了一个叫“榆樱院”的地方,作为小说中各色人物和他们的故事相遇、交汇的地点。她在后记中写:这样的院落在现实的哈尔滨道外区不止一处,它们是中华巴洛克风格的老建筑,历经百年,其貌苍苍,深藏在现代高楼下,看上去破败不堪,但每扇窗子和每道回廊,都有故事。它们不像中央大街黄金地段的各式老建筑,被政府全力保护和利用起来。这种半土半洋的建筑,身处百年前哈尔滨大鼠疫发生地,与这个区的新闻电影院一样,是引车卖浆者的乐园,夜夜上演地方戏,演绎着平民的悲喜剧。从这些遗留的历史建筑上,能看到它固守传统,又不甘于落伍的鲜明痕迹。这种艺术的挣扎,是城市的挣扎,也是生之挣扎吧。
小说出版后,迟子建接受了本刊的专访,在采访中她谈到自己对于书写一座城市的理解,比如为什么有的小说中会呈现真实的地名,有的却虚化?什么样的人物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灵魂?也谈到她对书写伤痛的态度,书写女性角色时对角色的选择和自我要求等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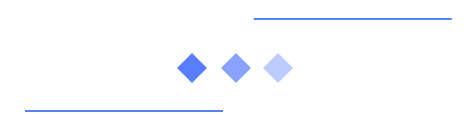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寻找别人,别人可能也在寻找我们
——专访作家迟子建
 作家迟子建(尹夕远 摄)
作家迟子建(尹夕远 摄)//
连一座城的缺点都爱,
你就愿意叫出它的名字
//
三联生活周刊:这本小说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,一块彩绘玻璃上一半是圣母怀抱的耶稣,一半是中国传统的门神。它是不是刚好代表了你所认识的哈尔滨?
迟子建:西方宗教的圣母玛利亚、耶稣与中国民间的门神神荼、郁垒同框,其实是东方与西方的交汇。他(她)们都是人类寄予福祉的守护神,只是姿态面貌不同而已,而这样的情节设计是用真实作为依据的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尔滨,因为侨民激增,所以各式教堂兴起。
因为西洋画师奇缺,有一些中国民间画师参与了教堂彩绘玻璃的绘制。中国民间画师对基督教、天主教等教义把握有难度,所以一些宗教题材的彩绘玻璃,画好了却没用,流传到民间。我就借用《烟火漫卷》,把它们镶嵌起来。小说中的《圣经》故事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,组合成一块隔断,伫立在榆樱院老宅的厨房,带着历史拼接的痕迹,感受着现实的人间烟火气。
而哈尔滨的历史,恰恰就像这两块拼接到一起的彩绘玻璃。它们与道外区的中华巴洛克建筑一样,借鉴西方,又固守传统;渴望着自由,又戴着镣铐;半是舒展半是挣扎,或者说是半梦半醒着,呈现着独有的风貌。

三联生活周刊:小说里面的人物刘光复见到这块彩绘玻璃之后,给出的评价是“基督的血,门神的泪”,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其中的含义?
迟子建:说个小插曲吧,在《烟火漫卷》新书分享会前,李敬泽、阿来、格非和我一起候场,为了试探李敬泽是否翻了这部书,我开玩笑让他讲出书中的一个细节。李敬泽说出的恰恰是:“基督的血,门神的泪”,而他的评价是“有意思”。在我的心目中,凡人有血泪,神人也有啊。而哪个神人,不是尘世催生的花朵呢?
三联生活周刊:在这部小说中你用很多笔墨通过建筑、街道,甚至音乐等展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样貌。作家阿来提到过,这种对城市形象真实的描述,对小说的内容、作家的书写都是有要求的。你在写作中有这样的体会吗?
迟子建:单纯地描写城市的建筑或是街道,没有人物的驻足,没有生灵的照拂,再美的风景也是死寂的。比如哈尔滨现存的各式老教堂,小说中的黄娥牵着孩子的手,决心在赴死前,把孩子托付给上帝——这是多么悲凉和绝望的托付啊,而教堂承载了一个母亲的无奈托付后,它们就不仅仅是城市景观了。
还有小说中写到一只雀鹰,小鹞子,它也是榆樱院的一员,如果没有它的栖息,榆樱院的树就少了神韵。再比如小说中写到的哈尔滨群力音乐厅,我让刘建国赶赴一场已在尾声的音乐会,而舞台上的演奏主角是他当年的女友,我让他在散场时抵达,遗憾错过——也必须错过,这座美轮美奂的音乐厅,就有了命运的撕裂感,所以描写它时会像塑造人一样,带着情感。
三联生活周刊:你认为那种将城市虚拟化的书写,比如A区、B市,是在追求某种真实,还是在回避真实?
迟子建:作家有时在小说中呈现真实地名,有时却又虚化,当然都有他们的考量。比如鲁迅也写过虚化的地名:S城、S门等。使用虚化地名我印象中频率最高的是张资平,他的小说连人物名字也用字母替代。当然他笔下那些K、V、W,都不及鲁迅先生同样以字母为人物命名、塑造的那个传世经典人物“阿Q”。
当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爱赋予一座城市、你针砭时弊有所忌惮时,在书写时也许需要A区、B市,无可厚非。可当你深爱一座城,甚至连它的缺点都爱,你就愿意叫出它的名字,不在乎别人怎样看待你对一座城的表达。其实无论北京、上海还是哈尔滨,只要进入小说,必然带有虚构的色彩。所以我笔下的哈尔滨,是现实世界的哈尔滨,更是我文学世界的哈尔滨。
三联生活周刊:你认为在城市题材的写作中,最重要的是什么?
迟子建:从文学层面来说,每个人对一座城的感受,都会带着各自的体温,所以写出的作品气质也就会不一样。《烟火漫卷》聚焦了一座城市,其中也涉及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当代城乡的变化,当然还钩沉了哈尔滨的历史风云。说起城市题材作品,就像开头我们谈到的,并不是因为你描写了城市的建筑、桥梁、街巷或者生活方式,它就有了神韵;也不是说你写了影剧院、咖啡店、奢侈品店、K歌的地方等外化的东西,它就是城市题材的作品了。
在我的理解中,当一座城的生灵——人与万物,同四季风霜、日月星辰,矛盾着,体贴着,排斥着,共融着,每颗心脏发出与众不同的跳动声,城市才是活的。比如我在小说里写到哈尔滨人爱出去洗澡的习惯,基本没涉及豪华浴场,多把笔触伸向了居民区中,那些热气缭绕的寻常百姓出入的小浴池。
城市题材的书写,不会因为你写了具有城市元素的东西,它就成立了,那充其量只是外观空间,或者符号化的东西。只有小说当中的人与万物,唱和着苏醒和沉睡,有了它们各自的声音和气味,这个城市才有灵魂。
三联生活周刊:对你来说,什么样的人物是更能体现一座城市的灵魂的?在你的笔下,既有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,也有一些外来者,尤其这个故事最为聚焦的“榆樱院”,更是外来者居多。
迟子建:我在《烟火漫卷》中,用大量篇幅写了黄娥这个人物,因为陆路交通飞速发展,水路交通消失——航运不通了,致使她过去的生活消失了,慢节奏的诗意的水上航行戛然而止,导致了她命运的悲剧转折,她才带着孩子,来到哈尔滨住进榆樱院。
我构建的小说中的榆樱院,是哈尔滨道外区的一个衰败的院落,但它在我心里,却是欣欣向荣的,因为这里住的人,从人物意义来说,是有光彩的。除了黄娥住这儿,还有来哈尔滨学唱二人转的年轻人也在这里,他们是寄居者,但你能说他们就不属于哈尔滨吗?我认为他们在融入这个城市的过程中,已经成为了哈尔滨人,他们和哈尔滨发生着千丝万缕的情感上的纠葛,虽然并不拥有哈尔滨的户籍,却是和这座城市休戚相关的人。
除了松花江流经哈尔滨,滋养着一直生活在这儿的于大卫、刘建国这样的人,我刚才提到的异乡人,也是看不见的活水,以一种遥远的方式滋养、丰富着这座城市,比如书里也写到的俄裔和犹太裔人。我觉得书写一座城市,首先要跨越行政和户籍这些概念的藩篱。哈尔滨的包容、接纳的城市特点一直都没变,各个历史时期,来这里开拓并把它认作故乡的人不在少数。
三联生活周刊:你已经有过很多部聚焦哈尔滨的作品,如今再写,还会感觉到和书写故乡大兴安岭的心理差异吗?
迟子建:基本没差别。我写《烟火漫卷》的时候,和哈尔滨完全没有隔阂,进入写作比较从容。几部写哈尔滨的作品,这部应该是融合度最高的。它涉及的历史较多,涵盖面也比较广,有相应的字数铺路,所以写它的时候酣畅淋漓,没有拘谨的感觉。如果是中篇,比如《晚安玫瑰》,可能一些细致的东西无法展开。
 迟子建说,《烟火漫卷》是一场大大的寻找(尹夕远 摄)
迟子建说,《烟火漫卷》是一场大大的寻找(尹夕远 摄)好的文学状态,是你进入创作之后,感觉自己是自由的骑士,疆域无边,任你驰骋,没有束缚感。其实写当下的东西是非常难的,因为每个读者都是现实的见证人,他们期待作品呈现的侧重点或审美点会千差万别。而写《白雪乌鸦》那样一场哈尔滨百年前的大鼠疫,没有读者是过来人,你做足功课,培养好情绪,把镜头推向从前,聚焦那个特定时代,读者很容易就有带入感。
但《烟火漫卷》不一样,写当代哈尔滨,必须搭建一个好的舞台,人物要在这上面演绎故事。我选择榆樱院作为主舞台,因为在哈尔滨的几个区里面,它是市井生活气息最浓的一个区域,我很喜欢。就像我在小说里写到二人转剧场,内容是真实的,二人转票价一般很便宜,10块20块的就可以进去,有的人蹬着三轮车运完货,穿个凉拖,买点小吃,就一身汗味地进剧场了。我去看二人转时也跟其他观众一样,买上一包瓜子,边嗑瓜子边欣赏演出,这好像已是看二人转约定俗成的习惯。瓜子皮扔了满地,最后清扫工把它扫走。30年前初来哈尔滨,我对它有些隔膜,生活上的水土不服,必然会造成文学上的水土不服,但当你了解了这座城市的历史,掌握了它的肌理,在文学表达上就比较自如了。
//
忍住哀痛的无声控诉,
才是大痛
//
三联生活周刊:刚才提到选择榆樱院是因为它市井生活最浓,我记得在谈小说《黄鸡白酒》的时候,你就说自己写的是世俗的烟火气。这本书名字里的“烟火”,也是同样的解释吗?有没有什么别的含义?
迟子建:书名里的“烟火”包含了多层含义,人间的烟火,天上的烟火,甚至地下的烟火等等。人间烟火,是现实中的榆樱院;天上的晚霞,那是小鹞子的烟火;地下的烟火,在小说中是卢木头的,你想想葬身鹰谷的卢木头,他戴着的那顶帽子,借着生灵的翅膀,借着风力、水力,山重水复的,能够漂流到松花江,抵达哈尔滨,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凄切和湿润的烟火吗?
三联生活周刊:这部小说中的人物,几乎无一例外地忍受着某种伤痛,用日常的眼光来看,其中很多伤痛是剧烈的,足以令人撕心裂肺,但你的人物对此都持有一种冷静和克制,为什么?
迟子建:我们谈到过哈尔滨这座城市和其他城市的不同,那么人物的伤痛也要符合城市的特点。比如犹太人谢普莲娜深爱的俄裔工程师,这在上世纪初是有迹可循的人物恋爱关系,他们爱情的悲剧背后,是历史的悲剧;再比如东北作为沦陷区,中日战争的创痛,在刘建国这个日本遗孤身上体现了。也就是说,出现在哈尔滨的伤痛点,要符合历史情境。
我写到人物伤痛的时候通常克制,这可能与我对命运的态度有关吧——遭受痛苦的时候,我的选择就是默默承受。比如18年前我爱人辞世的那个春天,我在家痛哭时,因为怕惊扰邻居,我会去洗手间,把洗脸池的水龙头打开,在哗哗的流水声中哭泣,这样的细节写进了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。
《烟火漫卷》中的人物哪怕痛到极点,都没有歇斯底里,当然如果确属人物需要,我也会让他们狂呼乱喊。但我觉得忍住哀痛的无声的控诉,才是大痛。如果写一个伤痕累累的人,你在他平静的外表下,能让读者看得见人物内心的伤痕,我觉得这才是了不起的。而即便伤痛的人,也不会每时每刻绷着伤痛这根弦,生活自有一股强大的惯性,一股强大的烟火气,裹挟着你走下去——活着。
//
日常远远比热点更有可信度
//
三联生活周刊:小说中的几个女性角色都让人印象很深,比如黄娥、刘骄华等等,但你的小说好像从来不会格外强调“女性”?能不能谈谈你对选择和书写女性角色的自我要求?
迟子建:我在小说里塑造过很多女性。性别意义上的人,通常是指男性和女性,所以写到女性难免要有男性,写到男性也难免要有女性,小说很难回避“女”字。但是我从没有在作品中刻意地在“女”字上做文章,而只把“她”作为小说当中的人物,她应该这样,或是应该那样。女性风格迥异,就连哭声和笑声,都是那么的不同。
比如《烟火漫卷》中的黄娥,城市是不可能诞生这样的人物的,当她在水路上驾驶小汽艇送男客的时候,立刻进入另一番情境,河边的树丛、河面的水鸟,以及那潺潺流水,像是她的自然同谋,勾引她出轨。别人觉得那是丑事,但她说是美事,这样的情节放在男性身上就不合适,因为女性在自然的天性上,更接近这样的人。黄娥是天然追求自由的人。黄娥的自然状态,是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双重的自然,当然是美好的。但是一个都市女性如果能够做到精神上的自然状态,已经挺好的了。
还有刘骄华,她在发现丈夫出轨后,很想出轨一次,报复丈夫,可她却找不到能和她出轨的人,这就是她遭遇的“痛点”。因为刘骄华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,她是一个好妻子、好母亲、好狱警。但所有的好,都没换来晚年她回归家庭后的“好”,她崩溃自弃,陷入绝望。
我写过很多老年女性,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《逝川》《晚安玫瑰》都写到老年女性,包括这本书里于大卫的母亲谢普莲娜,她们身上都有一种高贵。这可能和我的童年经历有关,我从小在外婆身边长大,她身上就有那种骨子里的高贵,这不是城市人或者有某种血统就能有的,天生的善良和大爱,让她显得高贵有尊严。
谢普莲娜这个犹太女人也是高贵的,刘建国弄丢了她的孙子,她从没责备过一次。
我也不会刻意为了一个女性热点话题,比如“Me Too”运动之类的去生造一个角色。我想“她们”能和我的小说组成一个生活的链条,她在这个链条里该是什么角色,就是什么角色。无论男性还是女性,人物应该符合小说的气场,有她该有的状态才是好的。在这点上日常远远比热点更有可信度。如果单独把“女性”拎出来,首先就把人物标签化了,这反倒成了问题。把“她们”放大以后以强光聚焦,摈弃自然状态,人物反而不真实了。而刻意强调“女”字,是为了求得哀怜,求得同情,求得赏识,还是求得什么?如果真有所求,那与女性追求的尊严和独立,又背道而驰了。
三联生活周刊:这本书借人物刘建国的经历写了一场“寻找”,我们可以说“寻找”就是这本书的主题吗?你想通过“寻找”表达什么?
迟子建:这本书是一场大大的寻找。我们去找别人,别人可能也在找我们。有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谁,这是生命最大的悲剧。就像刘建国几十年在找被他弄丢的朋友的孩子,但他却不知道自己生命的真相,他一直活在谜团中。在我们的生命中,有多少人值得寻找,又有多少人值得等待?而我们更应该想的是:我是谁?谁是我?
(本文刊载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20年46期)
本文地址:www.luolss777/caijing/yaowen/17432.html
上一篇:再见,爱笑的抗癌女孩霍九九!
下一篇:返回列表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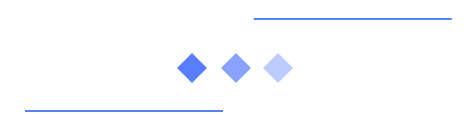
-

-
7月14日安徽省报告新冠肺炎疫情情况|新冠肺炎
2022年7月13日0-24时,安徽省报告无新增确诊病例,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。7月13日0-24
2022-12-14 08:36:36 luolss777.com -
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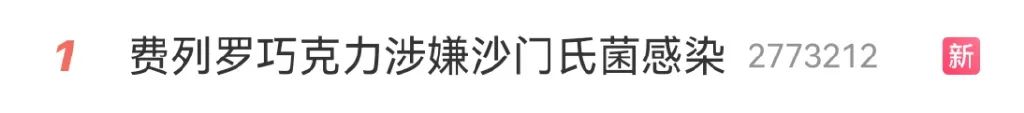
这款儿童超爱的零食别吃了!海外已出现病例……|中国
9日晚,“费列罗巧克力涉嫌沙门氏菌感染”登上微博热搜。据央视财经报道,近日,由于...
2022-12-14 08:35:49 luolss777.com
本文“迟子建:忍住哀痛的无声控诉,才是大痛”由777股票学习网(luolss777.com)首发,欢迎转载,转载请带上本文链接。
免责声明:777股票学习网(www.luolss777.com)发布的所有信息,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 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,投资者据此操作,风险请自担。部分内容文章及图 片来自互联网或自媒体,版权归属于原作者,不保证该信息(包括但不限 于文字、图片、图表及数据)的准确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、及时 性、原创性等,如无意侵犯媒体或个人知识产权,请联系我们或致函告之 ,本站将在第一时间处理。关注财经365公众号(caijing365wz),获取最优质的财经报道!
- 迟子建:忍住哀痛的无声控诉,才是大痛
- 再见,爱笑的抗癌女孩霍九九!
- 7月14日安徽省报告新冠肺炎疫情情况|新冠肺炎
- 女星代孕弃养丑闻背后:美国代孕已有产业链 有哪些中国客户?|代孕
- 那山、那水、那人家……
- 这款儿童超爱的零食别吃了!海外已出现病例……|中国
- 建构人生意义的四种方式
- 这双“时尚了千年”的老布鞋,穿上健康又保暖!
-
1/ 共享单车野蛮生长三年,回望却是遍地"尸体" 1
-
2/ 大疆的三亿“造星”计划 0
-
3/ 高大上的券商营业部,今年赚钱还不如家兰州拉面 0
-
4/ 基础设施补短板 万亿交通项目蓄势待发 0
-
5/ 抖音和微视打架时,网易和阿里也没闲着 0
-
6/ 股票|苹果破万亿,却没读懂其严重性! 0
-
7/ ofo海外市场持续撤退 卖身滴滴或为“自导自演” 0
-
8/ 百度真的能“再赢”谷歌吗? 0
-
9/ 现实的“西虹市首富”,后来怎样了? 0





